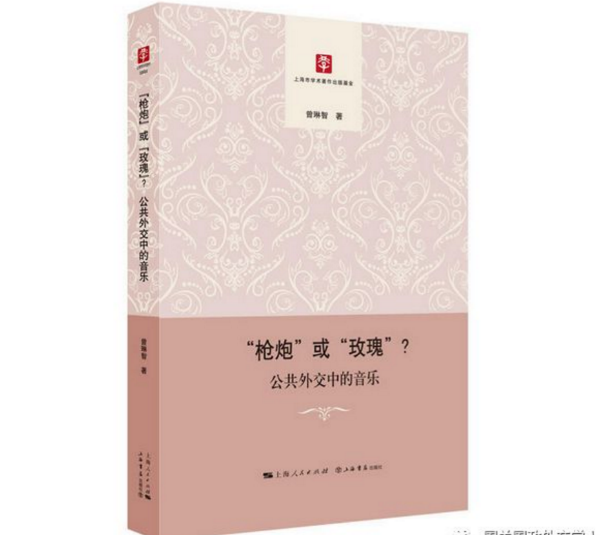
音乐不仅是一种蕴含情感的艺术,还能蕴含思想和观念。音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载着一国的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等,在增强一国政治影响力、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曾琳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一书构建了“音乐外交理论模型”,以中、美、俄三个大国的音乐外交互动作为案例,分析了音乐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政治先锋”“观念大使”“身份标识”“文化桥梁”角色,对如何将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剧,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虽仍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但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软实力”也越来 越被视为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因素。近年来,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文明 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主席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思想。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音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超越语言和国籍、深入人们生活的文明,一种蕴含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文化,其在公共外交中的潜力理应得到挖掘。
《“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一书便从音乐的特质出发,结合国际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理论,通过对政府文件与报告、学术 研究论文、新闻报道、深度采访等多种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从文献回溯、音 乐的“枪炮”外交分析、音乐的“玫瑰”外交分析、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奏鸣、音乐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弦外之音”几方面,系统地探索了音乐 和公共外交二者之间产生“共振”的内在脉络和深层缘由,“跨学科”地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如何发挥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启示。
构建音乐外交理论模型
为了证实音乐外交的重要意义,并探索音乐在公共外交中如何扮演重要角色,该书作者梳理了国内外大量关于公共外交、音乐艺术、国际政治中与音乐相关的文献,并突破学界现有研究基础,清晰地阐述了“音乐外交”的定义,同时创新性地提出“音乐外交理论模型建构图”。
首先,目前学界对于公共外交中的文化议题只是泛泛而谈,只从总体的角度探讨“文化是公共外交中构建公众观念与内容的一种重要方式”,缺乏对文化具体内容如音乐、美术、建筑等艺术形式的具体分析。《“枪炮” 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梳理了从古至今关于音乐艺术能推动国际关系的特质,如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乐”治国、“西东合集乐团”消除民族隔阂、《马赛曲》《欢乐颂》等音乐曾在国家冲突中发挥作用等,并基于此总结了音乐是一种聆听艺术、情感艺术和教化艺术,确认了其对处理国际关系具有潜在推动作用。从作者对“国际政治中的音乐”的研究现状的梳理结果来看,目前文献大多呈现音乐的工具理性层面,如音乐可作为“心理战工具”渗透政治观念、音乐为政治权力服务、音乐对缓解国际冲突和捍卫国际安全的影响等,而对于其价值理性的意义层面却未曾涉及。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领域的空白。
其次,该书给“音乐外交”下了一个详细具体且可操作性的定义:“音乐外交是以音乐为纽带的外交形式。它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的,通过乐器的演奏、人声的歌唱、音乐文化产品等途径,直接而广泛地接触外国政府或公众,向他国传播本国的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等,从而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 维护国家利益,分享不同文明的一种外交形式。”同时,作者也尝试构建“音乐外交理论模型建构图”,其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进攻性”音乐外交(音乐可作为“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和“防御性”音乐外交(音乐作为“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的理论内核,另一部分是音乐外交需要“双向沟通”、注重“长远影响”、可能“偏离政治理念”的理论外延,这些也是全书着重论述的几大维度。
探索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
正如书名所述,音乐在公共外交中或扮演“枪炮”角色,或扮演“玫瑰”角色。本书通过案例分析法,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和“中俄关系中的音乐化传播”为主,其他各国音乐外交的例子为辅,利用大量篇幅通俗易解地向读者展示了音乐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如何作为公共外交的手段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考、新见解。
“枪炮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先行兵”作用
本书认为音乐作为“先行兵”时,能在短期内消除他国公众的疑虑和误解,进行观念输入和情感冲击,起到试探对方政治意图、软化负面情绪、加强对本国认同的作用,主要承担“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的身份。
在“政治先锋”方面。当国家关系处于“冰点(不友好)”状态时, 音乐首先可以成为最好的试探先锋来试探敌意,如1956年冷战期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赴苏联演出时特意奏响苏联国歌以表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随后演奏美国国歌以试探对方意愿,苏联观众竟纷纷起立鼓掌,并在这一年美苏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其次,音乐可以用来释放善意,如1973年3月英国伦敦交响乐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演出团体,2007年德国欧斯那伯路克乐团在伊朗的交响乐演出结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交响乐限制,都展现了出访国与受访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愿,用音符唱响“和解之声”,开启友好对话。此外,音乐可以用来软化矛盾,如2011年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举办的爵士音乐会,就是在两国互信跌至“冰点”、巴基斯坦反美情绪高涨的时刻,促进两国人民互相沟通和理解的最简单直接的公共外交方式。在以上这些“破冰之旅”中,音乐的隐蔽性使其虽在内容本身不带有多少政治含义,却能传递某种政治同盟或合作的暗号,释放沟通的善意与信号,展现友好姿态。
在“观念大使”方面。当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出现分歧时, 音乐可以将文化观念和政治理念隐藏于音符之中,或进行意识形态进攻, 或平复文明冲突。本书主要通过阐述美国如何有意识、有策略地运用音乐作为其政治的“观念大使”出征他国,来支撑这一观点。如在冷战期间,美国派出黑人爵士乐团出访苏联、东欧、中东及非洲国家,借用黑人爵士乐承载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对公众进行价值观念渗透,培养“亲西方”的思想体系,并使其建立对美国形象的认知和好感。而在冷战后,美国也因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在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好感度下降,为此美国不仅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爵士乐团演出取悦他国听众、展现和平姿态,还推出“嘻哈大使”音乐交流计划,试图建立与伊斯兰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与当地音乐家友好交流、合作演出,表达了对世界不同文化、信仰和传统的尊敬,试图平复文明冲突,塑造本国良好形象。
“玫瑰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防御”作用
本书认为音乐作为“防御性工具”时,如同“玫瑰”余香,能通过分享不同文明吸引他国公众的兴趣和好感,从而起到塑造国家身份、增进相互信任的长远作用,主要承担“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的角色。
在“身份标识”方面。本书认为国歌和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家)是一个国家身份和形象的“听觉标识”,其所代表的国家理念和文化不仅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也影响着他者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认同。一方面,本书总结了世界各国的国歌,主要分为《义勇军进行曲》等表达捍卫国家独立的战歌,《金色的孟加拉》等歌唱祖国山川的赞歌,《天佑女王》等咏唱君王或上帝的颂歌三类。国歌的反复咏唱,不仅能凝聚国人人心,还能成为对外的一种身份宣誓,确立了“我是谁”“我代表谁”的国家“软边界”,无形间建立起一道国家的防御之墙。另一方面,本书也大量分析了各国民间音乐(家)的特征,认为其能最直接地反映该民族人民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思想情感,使他国公众通过民间音乐交流建立对该国的真切想象和认知。如朝鲜古老民谣《阿里郎》让人们认识了朝鲜民族坚韧不屈、浪漫直率的另一面;波兰钢琴家肖邦充满诗意的音乐作品则让世界人民认识了英勇又淳朴的波兰人民,在宣传波兰国家形象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桥梁”方面。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是搭建各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平台,使其以平等的方式对话、以文明的方式分享,本书便强调了音乐作为“文化桥梁”时,在公共外交中“听”和“分享”的过程。首先,由于民众常通过政府引导或媒体宣传来构建对于他国的“想象”,因此容易造成偏见和误读,而音乐的沟通与交流则可以使两国民众跨越国界“倾听”彼此的文化,使偏见和误读在审美愉悦中慢慢消解。如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组织为维也纳观众演出大型藏族歌舞诗《神奇的家园》,借此展现如今西藏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积极变化,使当地民众被西藏独特的文化内涵所震撼,也更客观而公正地了解西藏、了解中国。其次,音乐的共通性和包容性能嫁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助于分享文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认同。如宋祖英与加拿大著名歌手席琳·迪翁创新中西合璧的民歌《茉莉花》,美国著名萨克斯演奏家凯丽金将《茉莉花》改编成动人的萨克斯演奏曲,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斯塔夫·马勒从中国古诗中找到灵感完成其惊世作品《大地之歌》等,都是通过用外国乐器演奏本国音乐、将本国和他国音乐主题结合创造新作品等方式进行文化分享或融合。这种分享文明的过程还能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他国民族风俗、历史文化、国家性情,形成认知与好感,并逐渐培育认同与信任。
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该书并非仅仅停留在对音乐外交相对频繁的美、俄(苏)两国的分析, 还对目前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浅层的案例分析和抽象化的理论构建,还基于外国音乐外交的实践经验及中国音乐外交的现实情况,对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国内外纸质媒介2000年至2017年间对中国五个主流乐团的出访报道为例,考察音乐在我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该书总结了在两国建交前奏或建交纪念日、中外文化年(周)时期、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情况下,中国主流乐团往往会充当“外交先行者”,展示国家形象、搭建文化桥梁、传递合作友谊,且通常选用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表达人类共通情感的音乐类型,以赢得共鸣和认同。但中国更多注重的是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和各项重大活动中采用音乐外交,中国音乐外交更多承担的也是面向各国政要的政治使命,而缺乏对基层民众这一重要群体的重视,忽视了音乐交流、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的、日常的事业。为此,该书为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从传播主体而言,应注重音乐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和战略化管理。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扩大与非政府组织、海外机构、学术界、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不同层面群体的合作,运用各自不同优势拓宽音乐外交模式, 并适当弱化政府主导意图、淡化意识形态以让中国文化、中国形象更深入人心。其次,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音乐出访的内容、人员、战术等进行系统的战略管理,在保持文化年、国家年等固定的音乐外交形态的基础上,注重利用数字媒介与世界各地民众进行长远持续的、日常化的音乐交流与分享。如通过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普通民众合作、记录和分享音乐,建立长期友谊,润物细无声地讲述“中国故事”。
第二,从目标公众而言,应注重针对不同公众的需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实现本土化传播。特别对于中国近年来重点开展外交工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其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形态各异,应对目标国的目标受众进行深层细分,根据政治和经济背景、语言、文化价值观、音乐喜好、媒介接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如美国并非一直将代表国家音乐文化最高艺术水准的古典音乐作为外交的首选音乐类型,而是根据穆斯林青年喜欢“以说唱的方式表达重要的社会政治信息以及个人强烈的政治意识,追捧嘻哈音乐的反权威性和不羁”,选择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嘻哈大使”音乐外交项目,既注重了本民族的独特表达,又考虑了对象国的接受程度,实现有效的音乐外交。同时,还应格外注重与基层民众以及年轻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第三,从传播内容而言,应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融合性、共通性。首先,近年来中国江苏民歌《茉莉花》被频繁运用于国内重要事件和国际事务场合,但一首歌曲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形象。未来应充分挖掘56个民族的不同风土人情和文化财富进行音乐创作,因为多样化的音乐类型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公众关注中国。其次,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必然蕴含着大量吸引外国群体的传统价值和审美元素,应适当让这些中国元素融合西方的审美习惯进行针对性传播,以使中国理念通过音乐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认同。此外, 应更多地选择表达爱、命运、自然、人性等人类共通情感的音乐题材进行巡演,如表达英雄主义和对爱情坚守的《霸王别姬》、表达对人生终极意义考量和对世界道德深刻反思的《大地安魂曲》等,共通的音乐内容更能引起灵魂的碰撞、情感的共鸣,其所产生的亲近感也更有助于获得受访国公众对本国的好感与信任。
本书作者不仅具有优秀的音乐素养基础,还拥有宽广超前的国际视野。音乐和公共外交看似不同领域,但音乐所关乎的人性的“真”与国际关系所追求的“善”让二者存在某种特殊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音乐可以成为公共外交中的载体,承载一国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形象等进行传播,为本国发展创建观念和认同,增加国家“软权力”;另一方面,音乐可以成为世界通识的“语言”,创造对话与沟通的机会,潜移默化地消除误解、破除舆论、降低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促进国家、民族、世界向“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靠近。
当然,本书作者也并未将音乐夸大为“神丹妙药”,本书也承认了音乐外交的制约因素——由于音乐本身并不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传达的理念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治意图发生偏离从而疏离外交目的,且人们对一国音乐文化的好感也并不必然能转化为对其政府和权力主体的支持。因此, 当音乐作为公共外交手段时,只有与一国的外交政策相结合,并有规划、有策略地运用才能卓有成效。同时,切不可急于求成地追求音乐外交的短期利益,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魅力将在长远的未来绽放光彩。
作者: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